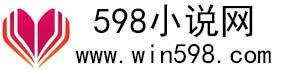第 4 节 宝樱(1/5)
谭宝樱这人违法犯罪的事儿没少干。
与我直接相关的有两件。
一是差点将我卖掉。
二是为我杀人。
1
我第一眼见到谭宝樱,就感觉她不像正经人。
粉色头发卷成稠密波浪,浓妆艳抹,举止轻佻,满嘴脏话。
偏偏双目生得空明澄澈,天真无邪。眼尾微微上翘,眉梢秀致,天然一段风情。
她站在树下,衣衫不整,仰起头朝我破口大骂:「他妈的谁家小孩,再偷看把你眼睛挖出来!傻逼!」
「对不起,我不是故意的。」我骑在树干上,抬手指向那条挂着尼龙绳结的树杈,声音细如蚊蚋,「我只是……来这里上吊。」
没开玩笑,就是字面意思。
谭宝樱唇角抽搐,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,嘴里仍旧不甘心地骂骂咧咧:「妈的真晦气,竟然碰到只死鬼。」
她暴躁地绕着树干狂走数圈,气得头发蓬乱,脸上脱妆严重,劣质粉底混着汗渍,晕出大片斑驳纹路。
「看什么看,还不快滚下来?」她终于忍不住重新怒吼起来。
按理讲我不该怕她,反正都是要自尽的人,但几乎是鬼使神差般,我被她周身气势震慑住,手脚并用回到地面。
那女人蹲在地上,过膝的裙摆层层叠叠垂落至地面,像是半开未开的花朵,粉面含羞,与她本人气质极不相称。
我的全部身家,那只由面粉袋缝成的破包,在她手里翻来覆去,挑挑拣拣,半天才在嘴角扯出一抹讥讽的笑:「靠,一分钱都没有,你他妈死了也是穷死鬼。」
「喂,知道刚才那男的给我开价多少?」她将正脸转向我,毫不避讳地比划起数字,「要不是你吓跑我的客人,耽误我做生意,我这单可就赚到了。说说吧,欠我的钱打算怎么还?」
「我、我不知道。」如果我有多余的钱,或许暂时还死不了。
「那你跟我走。」她站起身,使劲揪住我胸前褴褛衣襟,不由分说往前迈步。
我不明所以,被拽得踉踉跄跄:「去、去哪儿?」
「替我做事抵债。」她一字一句,咬牙切齿。
树林间风声猎猎,将她毛躁的粉色头发吹得狂乱飞舞,如同四散飘零的花蕊。
这就是我和谭宝樱初次相遇的场景。
2
我叫高繁,繁华的繁。
不过谭宝樱总嫌累赘,写成平凡的凡。她说这样简单大方,比原来花里胡哨的好看得多。
有时我想,能做个平凡的普通人,出生在不算富裕的家庭,父母吵吵闹闹,自己时常面临成长的烦恼,于我来讲,未尝不是一项难以企及的奢望。
自幼年起,我稍有记忆以来,就是在城郊那座亟待修葺的孤儿院中度过的。
抢不到饭菜,只能吃残羹冷炙。
做不来游戏,就蜷缩在光照稀缺的墙角。
我很早就意识到,在人类错综复杂的链接中,自己是不受欢迎、不被期待的存在。
画画是我唯一爱好,但从没上过一天正经课程。
搞艺术嘛,花钱如同碎钞机,哪里人人都负担得起。
十六岁时,我离开孤儿院开始自谋生路,头发剪得很短,穿宽松男款外套,外表邋里邋遢,像不修边幅的年轻男孩。
我去餐厅刷过碗,在自助银行睡过觉,最初数月居无定所四处流浪,但我还蛮开心的,因为可以随时画画不受打搅。
可即便是这样微不足道的快乐,对有些人来讲也是限时限量供给,这时候预支掉,以后就会被全部没收。
有天我突然发现,眼前经常模糊一片,什么都看不清,刚洗好的碗盘只剩满地碎片和沾满洗洁精泡沫滑溜溜的双手。
老板忍无可忍,匆匆支付上月薪水将我扫地出门。
我感到茫然又无助,生平头一回去医院。
大夫说我这是遗传性眼疾,失明风险极高,手术花销巨大,能不能治还另说。他问我有无家族病史。
「没有。」我困惑地嗫嚅着,「我没有家属。」
即便有,